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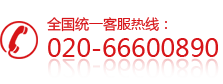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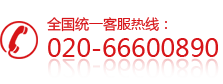
reen information
【裁判要旨】
为境外刺探、非法提供商业秘密罪应从以下要件进行认定:一是行为人侵犯的对象属于我国刑法保护的商业秘密;二是行为人客观上实施了刺探、非法提供商业秘密的行为;三是商业秘密系为境外机构、组织、人员刺探、提供,且行为人主观上知道。境外机构、组织包括其在我国境内设立的分支(代表)机构和分支组织、港澳台地区的机构和组织。行为人未被明确告知商业秘密系为境外刺探和提供,但主观上应当知道并持放任态度的,构成明知。
【基本案情】
郑某在A公司担任工程师一职,其通过签署的劳动合同、离职保密承诺书等承诺对A公司的商业秘密负有保密义务。
从A公司离职后,郑某接受B公司的邀请,成为B公司的行业专家顾问,并签署专家顾问协议。该协议约定,B公司系一家行业专业顾问咨询服务提供商,其合作客户包括证券公司、国内外私募基金和对冲基金、中国公募基金公司、国际知名管理咨询公司、知名大型企业和跨国公司等。郑某违反保密约定,利用自己掌握及向A公司员工刺探的信息,以A公司专家的名义,多次接受B公司的安排,为与A公司业务相似或具有竞争性业务的公司提供有偿咨询。
C公司(注册在中国的外国法人独资企业,股东为境外某公司)受境外的组织、人员委托,邀请郑某参加C公司委托B公司发起的有偿咨询活动。郑某在收到访谈提纲、且经几次更改过访谈时间后,接受了C公司的电话访谈,将其刺探掌握的有关A公司的商业秘密提供给了C公司,并非法获利2000余元。B公司在访谈结束后将访谈内容通过电子邮件发送给了C公司在香港的某工作人员。
【裁判结果】
一审法院认为,涉案商业信息是A公司付出创造性劳动后获得的成果,凝聚了众多研发人员的智慧,且对于A公司在国际和国内行业中的竞争力、未来的发展等具有重要影响,A公司从未公开发布(郑某亦确认上述信息属于A公司未公开的信息),因此该些信息并非所属领域相关人员普遍知悉和容易获得。A公司通过制定机密信息保护政策文本,与郑某签订劳动合同、离职保密承诺书等,对涉案商业信息采取了合理的保密措施。故涉案商业信息属于A公司的商业秘密。
郑某离职后,违反与A公司之间有关保守商业秘密的约定及A公司的保密制度,明知咨询方系境外组织,仍将从前同事处非法探知的涉案商业秘密,连同自己掌握的商业秘密一并提供给咨询方,其行为已构成为境外刺探、非法提供商业秘密罪,故判处有期徒刑2年6个月,并处罚金1万元。一审判决已生效。
【案例评析】
一刺探、非法提供商业秘密的认定
围绕本罪,应从以下要件进行认定:一是行为人侵犯的客体属于我国刑法保护的商业秘密;二是行为人客观上实施了窃取、刺探、收买、非法提供商业秘密的行为;三是商业秘密系向境外机构、组织、人员提供,且行为人主观上知道。因此,针对本案的行为,首先要对涉案信息是否属于商业秘密、行为人是否实施了刺探、非法提供的行为作出认定。
(1)关于商业秘密的认定问题。
刑法条文本身不再对商业秘密作定义,而直接援用反不正当竞争法相关规定,即构成商业秘密须同时具备秘密性、价值性和保密性这三个要件。对于本罪中商业秘密的认定,同样根据上述三个要件进行判断。但同时应当注意的是,侵犯商业秘密罪系情节犯,以情节严重为入罪要件。而本罪属于行为犯,侵害行为一旦实施完毕,便构成犯罪既遂。商业秘密的价值大小、权利人的损失或行为人的获利情况均不影响本罪的构成,仅属于本罪的量刑情节。对于本罪中情节严重的认定标准,目前尚无司法解释予以规定。本案中郑某的非法获利仅2000余元,但不影响对郑某的定罪。
(2)关于刺探、非法提供的认定问题。
刑法第219条之一规定了窃取、刺探、收买、非法提供等四种不法行为,只要实施了其中之一的,便构成本罪,属于选择性罪名。从获取手段看,窃取、刺探与收买,均是指原本未合法掌握商业秘密的行为人通过非法手段主动获取商业秘密,例如本案中郑某向其他员工刺探了其原本并不掌握的信息。非法提供则指行为人违反规定,将其已经合法知悉、保管或持有的商业秘密出售或透露给他人。从行为结果来看,窃取、刺探、收买、非法提供的商业秘密均被其他本不应知悉该商业秘密的机构、组织或人员所获取。在明知向境外提供的前提下,行为人采取何种手段、通过何种途径提供,则并不影响本罪的构成。
本案中,郑某系通过电话访谈的形式向C公司提供了其刺探、掌握的商业秘密,该电话访谈内容经由B公司整理后又通过电子邮件发送给了C公司。只要C公司获取了该商业秘密,郑某的不法行为即宣告完成,电话或电子邮件仅是信息的传递方式。
二境外机构、组织、人员的认定
从地理上看,我国国境、边境外的所有区域当然属于境外。设立在境外的其他国家或地区的政府、军队等官方机构,党派、社会团体、宗教团体等非盈利组织,企业、财团等盈利组织,取得外国国籍或无国籍的人员,都是本罪中境外机构、组织、人员的范畴。
2023年修订的《公司法》第247条规定,外国公司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设立的分支机构不具有中国法人资格,外国公司对其分支机构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进行经营活动承担民事责任。因此,虽然外国公司的分支机构系按照我国法律在我国设立,但其并不属于中国法人。《反间谍法实施细则》中对此亦作了明确的规定。这些分支机构、组织,以及在我国的境外人员,代表的是其他国家或地区的政治经济利益,为境外服务。我国市场内的商业秘密遭其非法获取的,属于本罪打击的范围。
关于在我国境内设立的外资企业是否应被认定为本罪中的境外组织的问题,则需作个案判断。一般而言,不宜对本罪的“境外”作扩大化解释。但结合相关证据,能证明是与境外母公司资源共享、信息共通的外资企业,特别是为了完成境外母公司的工作任务或委托而非法获取商业秘密的,应认定为本罪规制的境外组织。
从关境角度看,港澳台地区属于“境外”。本案中,郑某刺探、非法提供的商业秘密由我国外资企业常驻在香港的工作人员获取,可以认定为脱离了我国国内市场的控制,由境外相关机构获益,符合“境外”的认定。
三明知的认定
围绕本罪的主观状态问题,存在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行为人只要明知犯罪对象是商业秘密,且最终被境外获取,不必明知是否系为境外实施;另一种观点则认为,主观方面应当是双重明知,行为人不仅要认识到行为对象是商业秘密,还必须认识到是为境外提供商业秘密。笔者赞成第二种观点。
本案中,郑某辩称,其在接受访谈时并不明确知道对方的具体身份,但同时也承认,结合其从业经验和专业能力,能够意识到咨询方系境外机构,但未多想。郑某是否构成明知,如何推定郑某的应知状态,系本案争议焦点。刑法中的故意具备两个要件,一是认识因素,即明知自己的行为会发生危害社会的结果;二是意志因素,即希望或者放任危害结果的发生。对行为人的主观状态可以结合行为人的从业情况、行为人非法提供商业秘密的具体过程等进行判断。
在案证据显示,首先,郑某曾是A公司的技术人员,属于案涉行业的专业人员,对A公司的国内、国际市场地位有着清晰的认识。郑某亦承认,A公司是国内龙头企业,涉案经营秘密对国内竞争对手而言没有意义,只有境外同行业企业会感兴趣。其次,郑某在与B公司签署的协议中明确约定,B公司的客户,即郑某的咨询方,包括境外基金公司、咨询公司等。再次,郑某多次接受B公司的安排对外提供咨询,并承认其最初也怀疑咨询方中会有间谍组织,故而会在访谈前询问访谈目的,但时间一长,就不再追问。最后,郑某从接到案涉访谈提纲到实际接受访谈有很长一段准备时间,足以判断是否可以对外回答提纲所列问题。综合上述情节,尽管郑某并不知道咨询方具体姓甚名谁,但可认定郑某知道该对象是境外组织,仍接受采访并向其非法提供涉案商业秘密,放任危害结果的发生,符合本罪的主观构成要件。
【文献来源】倪红霞、杨岸松:《为境外刺探、非法提供商业秘密罪主客观要件的认定》,载《人民司法》2024年第20期

吴相茂律师
广东格林律师事务所监事、合伙人
广州市海珠区人民检察院听证员
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检察院听证员
广州市越秀区涉案企业合规第三方监督评估机制专业人员
广州黄埔区人民法院特邀调解员
广州商学院法学院实践指导教师
广州商学院职业生涯导师
广东省律师协会第十二届涉外刑事法律专业委员会委员
广东省破产管理人协会破产涉刑业务专业委员会委员
曾获广州市律师协会“2021年度优秀公益律师”“2022年度业务成果奖”
供稿 | 刑事辩护与刑事合规专业委员会 吴相茂
编辑 | 林凯珊
审核 | 葉素筠
